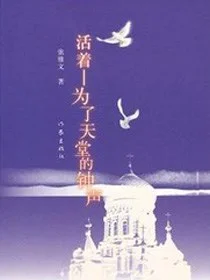作者 张雅文
一
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秋天。
肖思冰出命案的这天晚上,韩雪觉得外面的风刮得特猛,特瘆人,把电线刮得鬼哭狼嚎的嗷嗷直叫,好像有无数个冤魂在哭泣。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被刮起来,摔到玻璃窗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好像有人在敲窗。
她心想:这风刮得这么瘆人,是不是西伯利亚又来寒流了?
她害怕西伯利亚寒流,每次西伯利亚来寒流,她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恐惧之中。她一生中无法卸掉的生命之重,就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那是她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当年,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一个不知是法西斯党徒还是苏联特工的白俄流亡青年。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流亡青年在敌人的追杀中跑到她家里,却被她母亲发现了,用刀逼着他马上离开。就在他冲进暴风雨中的刹那,韩雪听到了枪声,发现了流亡青年丢弃在马路上的皮鞋及鲜血……
眼瞅着自己刚刚拥抱过,体温还没有散尽的恋人,就这样在她面前永远地消失了,留给她的是一双略带忧郁的灰蓝色眼睛,还有他那深情的求婚誓言:
“亲爱的,等战争一结束,我立刻带你走进圣·尼古拉大教堂,我相信你穿上婚纱,一定美得像天使一样!”
“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你愿意娶韩雪为妻吗?”他自问自答,“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爱她,呵护她,照顾她,直到生命尽头!”
她的精神崩溃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神经恍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害死了恋人,见着谁就向谁请罪:“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她错把教堂司祭当成岗察洛夫,与他私通并怀孕了。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飞行员。后来,混血儿子下落不明,丈夫被打成右派,她被收监……
她害怕回忆,每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像让她又经受一次疯狂与死亡一样。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害怕的东西,它却越像蛇一样缠着你,时不时地跳将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再领教一次痛不欲生的滋味儿。
多少年来,每逢遇到刮风下雨的夜晚,她就下意识地一次次地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外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敲窗?有几次,她甚至又出现了幻觉,发现有人影在风雨中晃动,仔细一瞅,原来是院子里的沙果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好像是人影似的。
这天晚上,又像往常一样,她又跑到窗前往外看,就在她掀开窗帘的刹那,发现有个黑影在窗外一闪就不见了。
她奇怪: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有人来趴窗子呢?
她想开门看看,又不敢,怕来坏人,只好趴着窗帘缝隙偷偷地盯着窗外,看看那人影会不会再次出现。很遗憾,瞅了半天也不见人影。
她回到电视前,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她喜欢这部电视剧,尤其喜欢电视剧里的那首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她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好像在写她,一辈子对爱情那么执着,执着得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男人似的。她不知这种执着到底是对还是错,她觉得人世间的好多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此刻,西伯利亚的冷风又勾痛了她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像往常一样,她又开始心绪烦躁,坐立不安,只见人影在屏幕上晃动,却不知电视里演的什么内容。
她觉得她这一辈子过得一团糟,糟透了。她就像上帝手中的一块面团,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肆意地揉来揉去,一直揉搓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上帝对她终于玩腻了,放手了。她也老了,退休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电话响,她以为是女儿婉如打来的。
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又送来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噩耗。
“什么?你、你……你说谁出了命案?”
韩雪变了调的惊叫声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在摆放着紫檀雕花衣柜的客厅里四处乱撞。她不相信老天爷会如此无情,总是跟她过不去。
“听着,我再说一遍!你家肖思冰出了命案。他害死了新婚妻子被逮捕了。看守所通知家属,给他送去被褥和洗漱用品!他给我们的电话是他妹妹肖婉如的。我们给肖婉如单位打电话,单位说她外出了,又给了你家的电话号码!这回听明白了吧?”
“听、听明白了。他、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啊?”
这无异是一张提前送达的死亡判决书,欠账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几年前,失踪多年的儿子肖思冰终于回来了,在道里中央大街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做母亲的总算可以放心了。就在几天前,1992年国庆节那天刚结婚,娶了一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媳妇。儿子并没有请她这位母亲去参加婚礼,让她很伤心。但是,看到从小就野性十足的儿子总算成家立业了,今后守着小媳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这个当母亲的也就省心了。没想到,这个冤家又闹出了人命。
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二
原来,这天晚上,肖思冰从海参崴谈生意提前一天回来了,特意买了一束红玫瑰,一进家门,却听见浴室里传来男女调情的嬉戏声,推开浴室门一看,只见小妻子正跟一个小白脸在雾气腾腾的芬兰浴盆里,模仿墙上电视录像里播放的外国男女做爱的镜头在做爱呢。
一看见肖思冰进来,小白脸吓得大惊失色,捂着小棒锤似的阳物仓皇逃走,不小心摔了个大仰巴叉。
小白脸逃走以后,肖思冰将手中的玫瑰花狠狠地摔进浴盆里,玫瑰花瓣散落在小妻子洁白如玉的肌肤上,就像滴落的一滴滴鲜血。肖思冰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种宿命的暗示。
肖思冰盯着那张令他心碎的脸,咬牙切齿地骂道:“小贱货,我最恨这种卑鄙的女人了!”
小妻子却一动未动,躺在浴盆里轻蔑地瞥他一眼,捏起两片玫瑰花瓣放在自己高耸的乳房上。
这个动作越发激起了肖思冰内心的激愤与冲动。他带回玫瑰花本想跟新婚妻子玩点儿浪漫,跟她来一次玫瑰浴。他准备像《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守猎者那样,将玫瑰花瓣摆在爱妻身上,他要吻遍爱妻的全身。他疯狂地爱着这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女人。
此刻,一种强烈的嫉妒与愤怒所激起的亢奋,使他变成了一只发情的公兽。他扒掉衣裤,咆哮着扑进浴盆:“你这个小骚货,不就是想让人干你吗?来吧,我他妈今天非干死你不可!来吧!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有什么权利骂我不要脸?”小妻子嗔笑道。
“我他妈是你丈夫!”
“啊呀,你弄疼我了!你倒轻点啊你!”小妻子娇嗲地喊着,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骂我不要脸,哼,哈尔滨谁不知道你妈是有名的大破鞋?”
正是这句话,触痛了肖思冰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
“你再说一遍!”一双大手像大叉子似的,叉住了小妻子细长的脖子。
“我再说十遍能咋的?你妈就是……”
这个因美丽而被男人宠坏了的小女子,以为丈夫在跟她开玩笑,以为他不过是下手重了点儿,以为……
命运就在这不经意间发生了生死变故。
他发现妻子的身子像面条似的瘫软在浴盆里,任他怎样呼喊,都毫无声息了。他抱着她在漂着玫瑰花瓣的浴盆里,呆呆地坐了四个小时,抽了一盒中华烟,最后操起了电话。
三
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于六十六岁的韩雪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痛苦更绝望、更令她撕心裂肺的呢?
“不——不——”她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放声大哭。可是,泪腺却像干涸多年的枯井,无论怎样哭嚎都挤不出一滴眼泪了。
她不明白,儿子刚结婚,为什么会干这种事?不能过就算了,何必要害死人家呀?这不是作死吗?儿啊,你咋这么糊涂啊?你才四十六岁,还有多少好日子在等着你呀?你这个冤家,妈真恨不得替你去死啊!
她瘫倒在沙发上,努力回忆着,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什么时候?
在她的记忆里,好多年没见到儿子了。儿子恨她,连结婚都不肯告诉她。两个孩子都像小鸟一样出窝了,飞走了,留在窝里的只有几根令老鸟无比眷恋的羽毛——一张挂在墙上的六寸照片。
那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唯一一张合影,1958年夏天拍的。
她哆哆嗦嗦地取下照片,用衣袖拂去照片上的灰尘,两张稚嫩的小脸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照片上,她一边一个搂着两个孩子。女儿肖婉如身穿娃娃领的花布拉吉。儿子肖思冰穿着无领海魂衫。虽说是黑白照片,但她仍然能看得出来,女儿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头黑发。儿子却长着一对黄眼珠,一头自来鬈的黄毛,一看就是串种了。
她抚摸着照片上儿子胖乎乎的脸蛋、高挺的鼻子、微微噘起的小嘴……
记得小时候,她最爱亲儿子白胖胖的小屁股,亲他骚烘烘的小鸡鸡,还亲他白面馒头似的小肚皮,一亲他就咯咯地笑个不停。现在,她多想再见见儿子,再亲亲儿子胡子拉碴的脸颊,再摸摸儿子钢刷子般的鬈毛啊!
她发现照片上的儿子在恶狠狠地盯着她,两只眼睛像匕首似的,咄咄逼人。不!那双眼睛更像法官手中的惊堂木,敲得当当直响,在追问着她这个母亲的灵魂。
她隐约觉得,儿子的命案很可能跟自己有关。一想到这儿,她心里不由得一阵战栗。她知道儿子恨她,死去的母亲也恨她。在他们眼里,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一个跳进松花江都洗不清罪恶的坏女人!
可是,她的满肚子委屈,又能冲谁去说呢?
一股又酸又涩的东西像游蛇似的从她心底爬出来,爬过喉咙,一直爬到舌尖上,最后汇成一声大吼,震得天棚嗡嗡直响:“老天爷啊!求求你快饶了我吧!”
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就像岗察洛夫被人追杀的那天晚上一样。
有几次,她又出现了短暂的精神恍惚,跑到窗前去掀开窗帘,看看外面是不是又打雷下雨了。她甚至听到了枪响,不过不是暴风雨中闷声闷气的枪声,而是从空旷得令人发憷的法场上传来的枪声,清脆而短促,带着一种近距离击中目标的决绝,眼前还恍恍惚惚地出现了一摊血,不过不是小精灵在雨中跳舞的那种殷红的血水,而是洒在荒郊野外那种干涸的血迹。
她忽然意识到,刚才看见的那个身影一定是儿子回来了,回家来跟她告别来了!
“心儿,我的心儿!妈知道你回来看妈了!”她呼喊着儿子的乳名,起身向门外奔去,“心儿,妈要救你!妈倾家荡产也要救你呀!心儿,妈不能没有你呀!我的心儿——”跑到门口却发现没穿外衣,又急忙回身取下衣帽架上的风衣。
她去找女儿肖婉如,外甥女方渺渺大学毕业,被分到区法院当助理审判员。她要跟她们商量怎么办,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就这样没命了。她拼老命也要救他。
坐在出租车里,她忽然想起母亲对她讲过的,韩家祖辈因风流引起的两条命案,她心想:难道这风流命案也能遗传吗?
(待续)